法国政治制度,法国政治制度思维导图
第五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四年这三十年期间,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分野,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八八四年,欧洲结束了对非洲殖民地的争执,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泛主义运动”(pan-movement)(如“泛日耳曼主义”运动、“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等,详见本书第四章——译注)。而一九一四年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在这三十年之间,欧洲是处于静寂的滞留状态,亚非两洲则有刺激性的发展。总而观之,这段时期有某些基本景观太相似于二十世纪所产生的极权政体之现象;因此,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认为这三十年正是酝酿了那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此外,它那滞留的状态,使我们更确定它依旧是十九世纪的一部份;在这里,我们实在无法避免以某些人士的聪慧眼光来观照这段看来似乎接近但却遥远的过去,这些睿智之士了解故事进展的终结,也认识到它割裂了欧洲历史绵延的潮流,犹如我们在二千年以前就了解一样。同时,也必须承认:对于这段时期,我们是怀着一股乡愁式的情感,仍然称它为“充满着安全的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甚至是恐怖的现象与事物均显现出一种温和的外貌,而且这个时代的人也能以一种礼仪来控制它们;鸟瞰这个时代的景观,会令人联想起活跃健康的气象。总而言之,不论我们与这段过去的时间是如何接近,对于本世纪见识过集中营生活与集体处死的人而言,这段时期所弥漫的气息以及西方历史的其它任何时代,均与现在的情境截然有别。

在帝国主义蓬勃滋长的时期,发生于欧洲的主要历史事件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直到现在,它是首次在历史上能不渴求任何政治统治权而能掌握经济优势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内与民族国家并行发展。所谓民族国家,既是驾乎阶级社会之上而统治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由是言之,甚至资产阶级建立自己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时,它也把政治的决策权拱手让给国家;唯有在民族国家无法适合资本主义往前拓展经济的架构时,国家与社会之间潜伏的纷争,才转变成公开的权力斗争。在帝国主义时期里,国家与资产阶级都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国家体制全然反抗帝国主义者贪求不厌、冷酷残暴,以及狂妄的行径;同时,资产阶级却一心一意想利用国家及其暴力的工具,来达成经济上的目标;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此两种情况均没有十全十美地成功。有一段时期,这两种情况有一极大的改变,是在甚么时期呢?就在德国的资产阶级把一切事物,投向希特勒的纳粹党作为赌注时,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亦企图利用“暴民”(the mob)来掌握政治统御权时,一切情形皆敢观了。资产阶级成功地摧毁了民族国家,但所赢得的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暴民证明了自己确实有能力以自己的立场来处理政务,也能肃清资产阶级,能摧毁跟资产阶级并行的其它所有的阶级与制度。
一、扩张与民族主义
“扩张既是一切”,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bodes)如是说,但他却堕入绝望的深渊,因为,每天夜晚,当他抬头遥望苍穹时,只见“这些星辰……这广大无涯的世界,均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并吞的;假若能力足够,我愿并吞所有的星辰”;他已觉触到运转着这个帝国主义的新时代的原理(在不到二十年之间,英国的殖民地增至四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六千六百万的居民;法国取得了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与二千六百万的人口;德国赢得了一个拥有百万平方英里之上地,与一千三百万人口的新帝国;比利时则因其国君而能获得九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与八百五十万的人口。)在智能光芒的照耀之下,罗德斯已洞识这项运动禀赋着疯狂的天性,也违反了人的限制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但洞见与悲切并没有政变他的政策;他也不需要这使他超乎一般野心商人的智能——他有明显的自大狂倾向。
“一个国家想玩弄世界性的政治就如一个人有自大狂一样”,尤金.李希特(Eugon Richter,德国进步党的领袖)在这段时期里说了这句话。他在“众议院”顽强反对俾斯麦的提议——支持私人公司建立贸易与航海基地;这显示出李希特比俾斯麦更不了解一个国家当时的经济需求。看来,那些反对或轻忽帝国主义的政治领袖,如德国的李希特、英国的葛莱斯敦(Gladstone)、法国的克莱孟梭(Clemenceau),是无法觉触到实相,无法了解到贸易与经济的活动已经迫使各个国家牵涉于世界政治的政策当中,民族国家的原则已被视为偏狭无知,同时,为正义公理而战也消失于历史舞台上了。
当时,任何政治家一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他唯一的报酬是迷惑与持续的困惑。因此,一八七一年俾斯麦拒绝法国企图以非洲的产业来交换亚尔萨斯卑洛林两省;二十年后,却以乌干达、尚西巴、维都三个地方向英国换取了海姑兰岛(Heligo-land——北海中的小岛)。犹如一位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对俾斯麦所说的:两个王权同沐浴于一只浴缸,并非不合情合理的。因此,在八十年代时,法国的帝国主义党派希望能派遣一支远征军驻扎埃及,俾能抗衡大英帝国,这项恳求,遭到克莱孟梭的坚决否定;可是,三十年后,为了英法同盟,却心甘情愿地把摩苏尔油田拱手让给大英帝国,因此,驻扎于埃及的克蓝玛(Cromer)公然指责葛莱斯敦是一个“无法担当起大英帝国命运的人”。

以既成的国家疆域为思考重心的政治家,对于帝国主义均抱着怀疑的态度,此种态度是合理的。他们宣称帝国主义是一项“海外的冒险事业”,一个政治家若企图干涉此项冒险事业以外的事务,则应该受到抨击。他们本能地觉触(并非真知灼见)到此种崭新的扩张运动(譬如谢莱登[Hubbe-schleiden]所称谓的“在赚钱的行业里,爱国热忱同时得到最完美的表达方式”,又如罗德斯所说的“国旗是一面对商业贸易极有帮助的旗子”)只会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征服,以及缔造帝国,是一件具有十足理由的不名誉之事,这两种行动唯有藉助于政府的力量,才可能完成。而政府——如同古罗马共和国——是奠基于法律之上;因此,随征服而来的,往往是压迫榨取,征服者强使相同的法律施行于被征服者的身上,借着此种强迫行为,企图统治与融合不同的民族。同文同种的人民主动地拥戴其政府,是民族国家建立的盘石(le plé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一个民族国家若缺乏此种主动拥戴的结合原理,那么,被征服的民族,必定走向强迫同化、强迫认同,而不是走向巩固结合与正义公理的道路,也就是说,政府必然退化成一个最暴虐的专制政体。罗伯斯比(Robespierre)很早就体认到此种情况,他如此说道:就算殖民者的态度是真诚的,它的致命伤依然是——自由。
“扩张”是一切政治的终极、永恒之目标,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核心观念;它既不是瞬间即逝的掳掠,也不意蕴着长期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在政治思想与行动的历史舞台上,它是一则崭新的观念。它那种新颖的、原创性的观念之所以令人产生惊异的感觉,是因为在政治中,创新的概念是很稀少的,故令人惊异。要之,其原因纯然在于这项观念毕竟不是政治学理可资言诠的,它的理路寻自于商业上的冒险。在冒险之中,“扩张”意指永无止境地拓展工业生产,这也显示出十九世纪经济贸易的特色。
在经济活动的畛域里,扩张是一项贴切的概念,因为工业成长既是一种周转不息的运作实体(a working reality)。扩张意指不断生产可运用,可消费的物品;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就宛如人为了他置身的存在世界,而不停地生产、建设、繁殖与改进一样。生产活动与经济成长也有缓慢下来的时刻,致使它们减缓的原因,大部分源自于政治行为,而非经济活动本身;这主要是因为生产,以及生产品的消费,完全依赖于由不同的政治体制所组成的不同民族。
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统治阶级开始反抗经济扩张遭受到国家的限制,帝国主义便应运而生。资产阶级为了经济的必然性,转而投靠政治;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资本主义的系统,他们也瞭解:此项系统的根本原理既是不停的经济成长。在渴望政治权力与不愿放弃资本主义系统的情况下,它就把这项原理强行于国家的政治之上,而且宣称——扩张既是国家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
资产阶级运用“为扩张而扩张”这项宣传口号来说服国家政府,而冀望它能迈向世界政治的途径,此项企图部份被实现。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此种新政策,使得众国家政府一开始进行扩张运动时,既陷入于共步同调与相互竞争的局势。从此一项事实之中,似乎可以察觉它本质上有限制与均衡的特性。在刚开始的阶段里,帝国主义可被如此描述:它是“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斗争。因此,就与“古代、中古时代的帝国观念”截然有别,在古代的帝国观念当中,“只有各个小城邦在盟主国统领下的相互结合,此种联邦政体……遍布于被承认的世界中”。然而,这样相互竞争仅仅是古代的残余物之一,它也可说是一种让步,让权给依旧流行的国家原理,依照这项原理,各个国家为了争取优越的地位而一争长短,人类也就居处于由这些相互较量的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之中。或者,它也对一项自由信仰让步,此信仰为:在一个国家消灭其它所有的国家之前,彼此的竞争就会自动地安置自身于一种早被安排妥当、稳固的均势局面中。可是,这种令人愉快的均衡局势,无论如何,很难是神秘的经济法则之必然结果。相反地它却全然依赖政治组织,甚至,更依赖警察制度,这使得相互竞争能免除武装暴力的使用。武装的商业团体——“帝国”——之间的竞争,为何在一个国家胜利而其它所有国家皆覆亡时才可能终止,实令人难解。一言以蔽之,“竞争”不仅是政治的原理,也是扩张的原理。而且“竞争”为了控制与限制,也急切地需求政治权力。
政治结构不同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无法毫不受限制地扩展,因为,它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无可限量的人类生产力上,就民族所缔造的政府与政制组织的形式而论,民族国家是最不适合于无限制的成长;因为,民族国家的基层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既所谓的共识),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由是言之,一个国家征服了另外的一个国家,并企图联合它时,往往很难赢取被征服的人民的赞助,纵然能够,也困难重重。没有一个民族在征服其它民族之后还能问心无愧,因为征服者自己也知道,征服意谓着将他们自以为优越的法律强行加于野蛮民族身上。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国家均认识到它的法律是根源于国家特有的实质,此种国家特有的实质一旦离开它的人民与疆界,则就不再是正确无讹的。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以一幅征服者的姿态展现的地方,就会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掌握自主权的渴望,此种情况将会摧挫缔造帝国的企图。由此观之,法国吞并了阿尔及利亚(Algeria),而把它曾作自己的一个行省;但是,法国却无法强使自己的法律行于当地阿拉伯人民的身上;它不得不尊重回教民族的法律,同时也得承认阿拉伯人民的“个别地位”,如此,就产生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疆域的荒谬混杂体。在法统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份,与塞纳-马恩省河流域的一行政区(the Departement de la Seine)一般,但事实上,其居民却不是法国人。
早期英国的“帝国缔造者”相信藉征服手段来达到永久统治,然而却连把其近邻——爱尔兰——纳入大英帝国或大不列颠国协这一广大的结构中也办不到。当爱尔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承认其自治领地位,也被承认为有资格成为大不列颠国协的一份子时,此种挫败就相当真实了——爱尔兰这个最古老的英属地、最新的自治领,竟扬言放弃其自治颌地位(于一九三七年),并断绝与大英帝国的所有联系(于拒绝参战的情况下)。英国所尊奉的法则——以征服来建立永久治理,“无法摧毁”爱尔兰(柴斯特东语),反而唤起了爱尔兰民族的抗拒精神,然而,却未激烈地激起英国本身的“昏睡的帝国主义天才”
英格兰联合王国的四个民族结构,不可能在短期间同化与结合被征服的民族;大不列颠国协从不是一个“各种民族的国协”而仅仅是英格兰联合王国的子嗣,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单一民族国家。散布与殖民经营并不是扩展,而只是移植政治结构;其结果是:被联结的政体(既殖民地),因为有着共同的历史传统,以及共同遵守的律法,依旧与它的故国紧密结合。爱尔兰是一极佳的例子,它证明了英格兰联合王国企图建立的一个由不同民族谐和生活在一起的帝国结构,是多么脆弱不稳固。我们也由此可了解,英国的特长并不是模仿古罗马缔结帝国的艺术,而是追随古希腊经营殖民地的模式。英国的殖民者在世界四大洲建立了由攫夺得来的新疆域,然而,这些新疆域并没有使英国扩展成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英国依旧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大不列颠国协的联邦结构是把国家政府的力量散布于全世界,此种建构方式令人心生钦羡之情。可是,此种联邦结构是否能有弹性地均衡下列两种情况,依旧是有待考察与了解的:一则是任何民族在缔造帝国时,本身遭遇到的固有困难;另一则是永久允许非不列颠的民族成为国协的“散布于世界各角落的伙伴”。印度虽已取得自治领的地位,但此种地位,在大战时却被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加以排斥。因此,所谓的自治领,被认为仅是一种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而已。
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征服行动的政治策略,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自拿破仑的美梦幻灭时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自此而后,征服者的权限便开始受到诅咒,同时,在边界纷争之中,征服的行为所扮演的角色也微不足道了,这不是来自于人道立场的考虑,而是出自于历史经验。拿破仑企图在法国国旗之下统一整个欧洲,但他失败了,这种挫败正显示出:由一个国家所发动的征服行动,若不是唤醒被征服民族的国家意识,起而顽强地反抗征服者;就是造成一种专制暴虐的统治。暴君的任何行动不需要人民的赞同,因此,暴虐的行动可能会很成功地统治其它别种的民族,纵然如此,专制政体若要保持其权力,则唯有彻底摧毁民族国家的体制。
近代的法国力图结合民权与帝权,也戮力去建立一具有古罗马意味的大帝国,这是与英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不同之所在。至少,法国独自努力地企图把国家的政治体制拓展成帝国的政治结构,也相信:“法兰西的国家正……撒播法兰西文明的福祉”;法国正力图以一种特别的态度,将海外的殖民地纳入国家的体制!之中,结成一体。耍凭借什么态度呢?既是:把被征服的民族当成“……既是弟兄,……也是臣民——在法兰西文明的博爱精神照耀之下,是弟兄;在法国之光芒的诫律底下,是臣民,是法国领导权的追随者”。当有色人种的代表在法国的议会中取得一席之位,而且阿尔及利亚变成为法国的一个行省时,此种企图部份被实现。
此种大胆的作为所带来的特殊结果,乃是为了国家的缘故而特别凶残地剥削海外殖民地。可是不论一切理论如问说,法兰西帝国确实是被高估的,因为它可以捍卫一个国家,同时,它的殖民地也被认为是一“军人之土”,因它可以产生一支土著军队来保卫法国的居民,对抗国家的敌人。朋加莱(Poincaré)于一九二三年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法国不是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是拥有一亿人口的国家”,这句话仅仅指出:“发现了可以用大量生产方法来生产制造枪炮之原料的经济形态”。一九一八年,克莱盂梭在和平会议中,坚持“假若法国将来受德国攻击,那么法国就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来征调黑人的部队,协助防御法国在欧洲的领土。”,虽然军事参谋部实践了这项计划;然而,诚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克莱孟梭并没有解除德国对法国的侵犯;相反地,他却结予这正招人怀疑的法兰西帝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与这种盲目绝望的民族主义相比较,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下的承诺——托管制度——看起来似乎更像民族自决的保护者;这似乎轻忽了一桩事实——他们一开始就因“间接统治”而误用了托管制度。所谓“间接统治”,就是允许殖民地总督“不是直接,而是循经土著部落与地方上的权威的媒介”,来统治这个民族。
英国力图逃避国家在缔造帝国时所禀承的言行不一的危险;英国企图缔造一个大帝国,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凡是有关文化、宗教与法律,都听任被征服民族的自行处置,也一再限制英国的法律与文化散播于其上。然而,此种作风却无法防止殖民地的民族意识蓬勃地发展,也无法消弭那宣扬自主权与独立权的扰嚷鼎沸之声——纵然可以多多少少延缓这种过程的拓展。同时,这种作风也仅仅会强化新起一代的帝国主义者的一种根本意识——此意识并非瞬间既逝,而是根深柢固的;是什么意识呢?即是:某一类人更优秀的意识,“高尚教养”轻蔑“卑微出身”的意识。因这种意识,更激扬起被征服民族为自由而战的热情,也使它们藐视英国的统治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任职于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对于当地的土著民族总是抱着高高在上的态度,尽管有些人“把土著民族当作一民族而真正尊重,甚至喜爱他们,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土著民族能够不需要白人监督治理自己”,因此,“土著”便只得相信自己是被蔑视。
帝国主义并非建立帝国,扩张也不是征服。英国的征服者,这些“印度法律的破坏者”(柏克语)与统治印度民族的行政官、英国金钱的输出者,绝少有相似之处。这些行政官与金钱的输出者,如果从颁布法令的身份转而为法律的制定者,那么他们可能成为帝国的缔造者。然而,关键在于:不列颠国家对此并不关心,也几乎不支持他们。政府官员紧跟着有帝国主义心态的商人身后来到殖民地,他们希望“非洲由非洲的人民来治理”,他们之中绝少有人,如尼柯逊所谓的:拥有“童呆性的理想”,企图帮助非洲的人民,使他们成为“更美好的非洲人”——不论这意谓着什么;在任何情况下,英国的政府官员都“不愿应用本国的管理与政治采统来治理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更不愿意把不列颠散布于世界各角落的殖民地与不列颠国家紧密相结合。
在真正的帝国结构里,祖国(意指被统领的殖民地国家——译注)的政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归纳于帝国之中;与此相背反的帝国主义,其特色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两者仍旧是相分隔的,纵然允许国家的政制插手控制。这种彼此分隔的原动力是自大与尊敬两相混合的杂混体。任职于海外殖民地的总督一旦面对“落后地区的民族”或者“低教养的人民”,就不由自主兴起一股新的狂妄自大的感觉,而且也发现:这种感觉与国内传统典型的政治家的感觉是相关联的。国内传统典型的政治家一致觉察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法律强加于外地民族的身上。然而,如同事物的本质,狂妄自大自然而然就转变成为统治妁工具。另一方面,尊敬的心意却依然潜伏于消极的状态之中,既然无法构想出一套使人民能和谐生活的新途径,所以只能在一定的限制范围之内,以命令(decrees,命令与法律之间是有区分的,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一译注)来牵制那冷酷无情的帝国主义者。对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治家的牵制帝国主义,我们是抱着赞赏的态度;但是我们对于殖民地的人民也应当尽一种义务,那就是,使这些被西方统治的人民,不论如何,均能从被统治中得到利益。事实如何呢?从事殖民地事业的人从来就没有停止去防御“毫无经验的大多数人”——国家——的干涉,国家的此种干涉既是力图以“模仿的导向”(亦既:依照国内普遍运行的公理,正义与自由原则的治理方向)来压制“经验丰富的少数人”——帝国主义的殖民总督。
上面已说过,民族国家是比其它任何政治体制,更需要以疆域与征服的限制底观点来加以界定;同时,我们也觉照到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却在民族国家之中蓬勃滋长。由是观之,此历史现象是一范俐,足以说明原因与结果之间那种看起来似乎是不相称的景观,这种景观已成为近代史的一种显明标记;近代历史的术语,其广泛的混淆不清均源自于此种不相称。由于和古代帝国相比较,由于把征服误认为扩张,由于忽略了国协与帝国之间的相异处(在帝国主义发生之前,西方的历史家将这种不同称为产业与拓垦地、殖民地与托管地、殖民主义与帝国之间的相异;换言之,既忽略了(英国)移民与(英国)金钱的输出之间的不同,历史家力图罔顾一项扰人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呢?既是:发生于近代史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看起来虽似一个个小鼹鼠丘,却已堆聚成一座座巍峩大山。
少数的资本家为了新起的投资或然率,为了因应“富豪”的获利动机,以及“贫无立维之地的人”的投机本能,遂遍及全球去策动他们的掠夺事业;当代的历史家目睹此种景观,就把帝国主义包围着一层古罗马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古旧但富丽堂皇的外衣,这富丽堂皇的色彩,使得随后发生的事件更让人可以容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不成比率,在一项有名的,而不幸成真的评论中,毫无隐蔽地揭露出来。是什么评论呢?那就是:不列颠帝国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被建立起来。为铲除希特勒竞需发动世界大战,更能清楚地表达此种因果之间不相称的比率;这场战争的确是命人羞愧的,因为它是一场闹剧。在德雷佛事件(Dfeyfus Afrair)发生时——一个国家的美好元素,被用来从事一项起始是卑鄙而以闹剧终场的斗争——与此相似的事物已明显表露。
帝国主义唯一崇伟处在于: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而遭受的挫败。此种冷漠的反抗,其悲剧性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商人可影响腐蚀许多的国家代表;而在于一项比腐蚀更败坏的事实,既是:那些不受帝国主义商人影响的国家代表却相信帝国主义是引导世界政治的唯一途径。由于所有国家急迫需要航海驿站与物质资源,遂坚信缔造同盟与扩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但这些国家全然不了解:单纯为贸易之故而设立的贸易与航海驿站的古老基架,是不同于扩张的新政策。它们一致相信罗德斯的一句话:“醒醒吧!一桩事实摆在眼前:除非你们能扩展世界的贸易,否则无以为生”,“你们贸易的范围在于整个世界,你们生命活动的舞台,不在英格兰,而在于整个世界”;因此,它们“必须处理扩张的问题,以及保有整个世界”;在盲味的情况下,它们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共犯,而且它们也应当因“帝国主义”而被抨击,被批判。举一个例子来说,克莱孟梭,他极度担忧法国民族的未来,遂投靠“帝国主义者”,冀望殖民地的人力可以护卫法国公民免受侵犯的威胁。
在拥有殖民地产业的所有西欧国家里,议会与自由出版事业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良心,不论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或者是荷兰,此种国家良心虽然时时发生作用,但都受到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埋怨与阻挠。在英国,为了区分受议会控制的伦敦帝国政府与殖民地行政官员两者间相异之处,此种阻挠的影响力遂被称之为“帝国的因素”;借着这样的名称礼赞帝国主义尚存有正义公理的残余物,而事实上正义公理却是帝国主义一心一意想抹煞的。在政治上,“帝国因素”表达于一项概念之中,即是:土著民族不但需要保护,也需要循就此方式而由英国人的“帝国的议会”来代表它们。在这里,英国缔造帝国的经验与法国的相当接近,纵然英法两国从来没有给予殖民地人民任何确实的代表权。毕竟,这两个国家希望整个国家成为其征服人民的信托机构,而且,试图利用各种方法尽力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这倒是真的。
“帝国因素”(毋宁说是“国家因素”)的代表与殖民地行政官员之间的冲突,宛如一条线,贯穿整个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历史。一八九六年,克蓝玛执政埃及时,对薛利斯柏利爵士(Lord Salisbury)如此祈祷道:“解救我!使我脱离英国行政区”,这段“祈祷文”一再重复着,直到一九二○年代激进的帝国主义党派因受到丧失印度的威胁,而公开指责它所代表的国家与一切事物的时候为止。“在英格兰舆论之前公正地裁决印度政府的存在”,这句话往往激怒了帝国主义者;因为这使得他们无法进行“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c massacrcs)的手段,这种激烈的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经常用来平定各殖民地,而且也确实可能阻挠印度的独立。
在德国,同样的敌对状态也产生于国家代表与非洲殖民官员之间。一八九七年,卡尔.彼德(Carl Peters)因为残酷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人民,而被撤除服务于德属南非的职位,并被召返国。吉莫勒总督(Governor Zimmerer)也是如此。一九○五年,殖民地区的部落酋长首次在德国议会中苦诉他们的不满,其结果,每当殖民总督要将他们下狱时,德国政府就加以干涉。
同样情况也发生于法国殖民统治。受巴黎政府派任的殖民总督,若非受制于来自殖民地的压力(如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便是拒绝改善处理土著民族的方式;这些土著人民宣称自己是受“(他们)政府脆弱的民主原则”所鼓动。在任何地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官员时常感觉到:控制一个国家或民族是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同时对他们的统治也构成威胁。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者的观点全然是正确的。比起那些既抗议政府的命令与独断官僚政体,又冀望永远保留着海外产业而俾能祟耀国家的人,帝国主义是更能了解近代治理殖民地民族的条件,他们也比民族主义者更能了解国家体制是没有能力缔造一个帝国的。他们更清楚的理解到一个国家及其征服民族,两者发展的步调,如果循其本然法则而进,其结果便是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征服者的挫败。因此,法国经常力图结合(被征服)民族的愿望与帝国的缔造,英国则于一八八○年代明白地宜称自已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既使受本国人民的民主政制所约束。两者比较,英国所运用的方法是较成功的。
标签: 法国政治制度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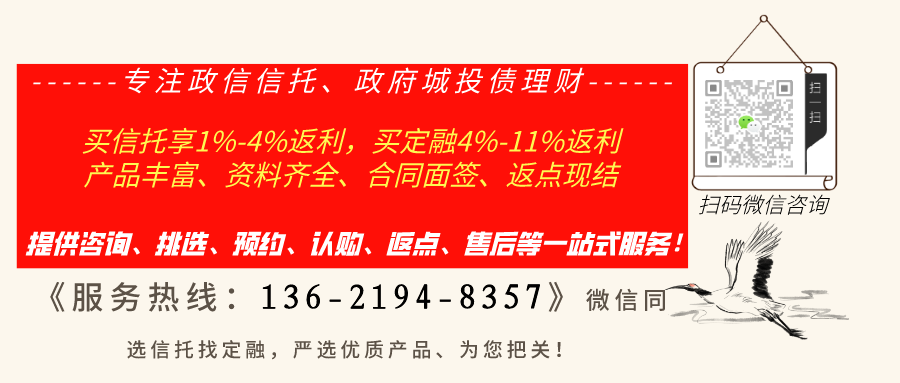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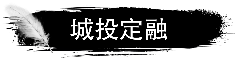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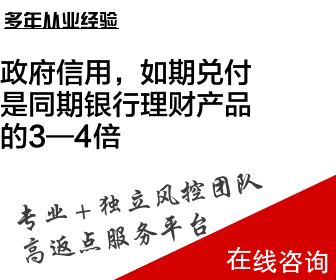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