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法,美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法的区别
作者按:2018年“阜兴系”事件中,由于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失联,导致总规模近300亿元的上百只私募基金出现了严重风险,就托管人是否应当基于共同受托制度而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1],基金业协会[2]与银行业协会[3]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表态,引发了理论界及实务界关于托管人法律地位与责任边界的广泛讨论。对此,证监会在其最新发布的《托管业务管理办法(2020)》中只是细化了托管人的职责内容,未明确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与责任边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监管部门在制度层面准确回应核心争议。规范的模糊化也导致司法实践往往避开对基金托管人法律地位的认定,而是径直以基金合同、托管合同约定为限认定其责任范围[4],致使托管人的基金治理功能沦为形骸,基金暴雷事件层出不穷。
为回应上述问题,考虑到基金托管人的保管职责在实践中争议极少,本文集中讨论了托管人的独立地位与监督责任,具体包括托管人的法律地位、职责范围、尽职履责的认定标准及违反监督义务的责任承担方式。本文的核心观点为:
1. 基金托管人并非共同受托人,而是唯一的信托受托人,管理人则系基于事实的受信人,在欠缺共同共有及客观行为共同等当然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基础时,应当依据托管人的履职情况独立地课以其违信责任。
2. 托管人的监督范围包括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及信义规范。就实务中极为普遍的免责条款,公募基金合同仅可细化托管人监督职责,私募基金合同可部分免除但不得整体免除。
3. 托管人的监督标准不应机械化地分割为形式监督和实质监督,而应先将监督标准由低至高谱系化为形式齐备性、形式有效性、合约性、合法合规性及合理性审查等不同层次的监督标准,并综合考虑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及托管人监督能力、监督成本、管理费率、法律风险等要素,在具体案件中动态选定托管人的监督标准。
4. 托管人违信责任的承担方式取决于其与管理人的过错形态。在两者以意思联络共同行为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管理人故意违信,托管人因过失监督不力而成为损害发生的间接因素时,托管人承担补充责任;在两者均系过失,或管理人过失、托管人故意时,由于两者均无法单独造成损害结果,应当承担按份责任。在后两种情形下,还需要考虑托管人的过错程度及托管费的多寡,合理确定其责任范围,以免戕害托管行业的发展。
篇幅所限,本文分上下两篇推送,上篇内容为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与监督范围分析,下篇则在确定其监督范围的基础上,讨论其履职标准与违反此标准后的责任承担。
一、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与独立责任
我国的基金架构包括公司型、契约型和有限合伙型[5]。就公司型及有限合伙型基金,由于基金系独立的主体,享有基金财产的所有权,基金托管人并非与管理人或投资人,而是直接与基金签订托管合同,本文认为,将其界定为保管人更加符合其功能定位。但是契约型基金[6]则有所不同,契约型基金的当事人包括基金投资人、管理人与托管人,《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 条第2 款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关于这一条文的含义,全国人大在该法的释义将其界定为“共同受托人”,[7]而根据《信托法》第31 条、第32 条规定,受托人为两人以上的,属于共同受托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不乏有观点(甚至趋于主流观点)将我国契约型基金的结构理解为共同受托制度,并要求托管人就管理人的违信行为承担连带责任。[8]如在“阜兴系”案中,基金业协会洪磊会长即主张托管人应履行共同受托职责,对管理人违信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9]
(一)不应依共同受托制度连带认定托管人责任
本文认为,基金托管人的法律地位并非共同受托人。共同受托制度包括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在财产关系上,共同受托人共同共有信托财产;第二,在事务管理上,共同受托人应共同处理信托事务,即所谓的客观行为共同;第三,在责任承担上,共同受托人原则上应承担连带责任,此系受托人客观行为共同在责任层面的延伸,也系财产共同共有的逻辑必然。[10]
然在基金领域,首先,基金财产由基金托管人持有,并非其与管理人共同共有;其次,管理人的主要职责是投资运营管理,托管人的主要职责是资产保管与投资监督,两项职责迥异,无共同处理事务之可能;再次,根据《基金法》第145 条第2 款[11],基金领域以分别责任为原则,连带责任为例外。
因此,在财产关系、事务处理及责任承担三个维度上,契约型基金的法律关系与共同受托制度均截然不同,在确立两者关系时,不应依据共同受托制度连带认定托管人责任,而应结合信托法理、具体职能,分别界定两者的法律地位与责任形态。
(二)应依双受信人制独立认定托管人责任
然分析至此尚不足以解决问题,既然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并非共同受托人,那么两者之间究系何种法律关系?基金托管人是否应独立承担责任?此种独立责任的法理基础何在?
对此,从各家争鸣来看,主要有五种观点:1 、基金托管人系保管受托人,负责持有基金资产,基金管理人系管理受托人,负责基金的投资运营,两者分担受托人的职责,系双受托人制,或称之为特殊的共同受托人,故并非当然承担连带责任;[12]2、基金投资人与管理人、托管人的法律关系不同,与管理人之间系信托关系,与托管人之间系委托关系[13];3、基金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系信义关系,与托管人之间系合同关系,托管人从形式、功能都不符合信义关系的特征[14];4、基金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是委托信义关系[15],托管人是唯一信托受托人;5、认同基金托管人系唯一受托人,但认为管理人是基于事实的受信人[16]。
本文认为,基金托管人作为唯一持有基金财产之人,其法律地位系信托受托人,基金管理人则系基于事实的受信人,故两者欠缺共同共有及客观共同行为等连带责任的制度基础,自然应当依据其履职行为独立判断其责任。
1. 基金托管人系信托受托人
在信托制度中,信托生效的核心要素为财产所有权的移转。[17]因此判断受托人的核心标准即其是否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基金法》第29 条规定:“基金托管人履行下列职责……(二)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帐户和证券帐户……”,实践中,基金账户往往是托管人以基金的名义或基金和自己联名的方式开立,因此,托管人作为唯一的基金财产所有者,其法律地位应系信托受托人。
虽有观点将托管人法律地位界定为合同当事人进而认为其不负有信义义务,实践中亦普遍认为托管人的监督范围以法律明确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为限,而不得补充适用信义义务。但笔者认为,托管人完全符合信义关系的三项标准——信任[18]、承诺[19]与自由裁量权。尤为重要的是,按照Paul 教授的观点,信义关系的核心为自由裁量权的让渡[20],但权力让渡的程度是可变的[21],与基金管理人相比,基金托管人被投资人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小,但是其监督义务所要求的自由裁量权远大于被动信托,自然不属于被动信托,更不可能是合同义务。托管人的监督职责贯穿基金“募- 投- 管- 退”的全流程,从资金募集,到投资指令的执行,再到投后运营管理及清算退出,基金托管人的每一次监督行为都需要其作出决策,如是否执行投资指令、核准收益分配、复核基金报告等等,均系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2. 基金管理人系基于事实的受信人
基金管理人未持有基金财产,其法律地位无法界定为信托受托人,但其基于自由裁量权的让渡而负有信义义务,那么其法律地位应该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应将其界定为基于事实的受信人。
受信人(fiduciary )一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fiducia ,[22]这一衡平法术语随着信托法的引入,在我国被广泛使用,然而由于基础概念的缺失以及法律术语翻译的差异,在适用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歧义[23]。除了翻译上的混乱外,学界多将受信人(fiduciary )等同于受托人(trustee ),忽略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24]从《元照英美法词典》及《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的注释来看,受托人概念强调其对信托财产的排他性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更为严格的信义义务,受信人作为受托人的上位概念,较受托人更为宽泛和灵活,[25]其外延除公司、代理、合伙等被广泛认可业已定型的基于身份的受信人(status-based fiduciaries )外,还包括从某种关系的具体情况(信赖、自由裁量权,机密、创意等)中产生的基于事实的受信人(fact-based fiduciaries )[26],例如扎克伯格窃用Facebook 的创意虽未违反合同义务,创意也非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但却违反了基于事实而产生的信义义务[27]。
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因与投资人之间具有信任、脆弱性、自由裁量权让渡等特征,在英美法上往往被视为定型化的受信人的一种 [28]。但是在我国法上,由于受信人、信义法等概念尚未得到普遍承认,无法将管理人归入业已定型的受信人关系中,故应将其界定为基于事实的受信人。
(三)可能面临的质疑及进一步澄清
鉴于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认为,我国契约型基金的组织架构可以通过英国法上的保管受托人和管理受托人概念提供解释,[ 29] 实有必要对此予以回应。根据英国《1906 年公共受托人法》(Public Trustee Act 1906 )第4 条第2 款,管理受托人享有经营管理权,但并非财产所有权人,保管受托人则持有并保管信托财产,[30]两者职责迥异,系法律的特别安排,因此无需按照共同受托制度承担连带责任。受该法影响,新西兰《1956 年受托人法》第50 条及毛里求斯《2001 年信托法》第25 条均规定,信托财产应归属保管受托人,管理权则归属于管理受托人。[31]
本文认为,上述立法模式实系以法律拟制的方法暂时绕开信托法的障碍,但是并不符合信托法理且存在体系矛盾,不应将其适用于我国基金法。如果认为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系对受托人概念的分解,逻辑上就需要建构“不完全受托人”的概念,这样一来,反而会招致更多需要解决的理论难题,譬如,如何准确界定不完全受托人?共同受托人制度中的受托人之一能否界定为不完全受托人?不完全受托人的信义义务标准与受托人是否一致?凡此种种,皆系“受托人职能分解说”的弊端,在有更符合信托法理解释路径的情形下,无需借道法律拟制。更重要的是,在创设这一制度的英国《1906 年公共受托人法》中,亦明确将单位信托(英国法上的契约型基金,其架构与我国契约型基金极为相似)排除在“受托人职能分解说”的适用范围之外,即保管受托人、管理受托人是法律拟制的特殊主体,只有符合该法规定的要求后才可以适用,而单位信托作为私法领域的契约型基金,并不符合该法的适用范围,[32]故在英国衡平法上,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往往被界定为受信人(Fiduciary ),托管人才系唯一的受托人(Trustee )。[33]
二、托管人的监督范围
(一)法定职责范围
根据《基金法》第36 条、第37 条及《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17 条、第21 条,基金托管人的法定职责包括安全保管基金财产及其衍生的开设账户、分别设置账户、保存活动资料、清算交割等保管职责,以及复核投资指令、基金净值、申购赎回、收益分配、信息披露报告、出具托管报告、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等监督职责。
(二)基金合同限缩托管人监督职责的边界
除上述法定职责外,根据《基金法》第3 条第2 款及《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21 条,托管人的监督职责还可能来源于基金合同约定。当然,实践中更为普遍的是,由于投资人的弱势地位,基金合同往往会减轻甚至免除托管人的监督职责。尤其私募领域的免责条款十分常见,以阜兴系事件为例,该案的基金合同就部分免除了托管人的监督义务。[34]因此,基金领域免责条款的效力及边界即成为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认为,公募基金的监督规范已被法律确定为强制性规范,无特约免除之空间,仅得将抽象的监督义务予以细化。然私募基金监督规范的性质尚不明晰,从信托法理上应当允许当事人特定(部分)免除,但不得概括(完全)免除。
1. 公募基金合同可细化监督义务
《基金法》第36 条及第37 条明确规定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应当”对投资指令、基金净值、申购赎回、信息披露等基金管理事项进行监督。在公募基金中,基于基金市场的涉众性以及强监管需求,托管人所负担的法定监督职责系强制性规范,当事人无权通过基金合同与托管合同对其进行减弱或免除。但是这并不是说完全排除当事人的自治空间,由于基金法对监督内容及监督程序的规定趋于原则化及模糊化,基金合同及托管合同亦可对此进行细化[35],如明确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基金净值的核算方式等。
2. 私募基金合同可部分免除监督义务
本文认为,私募基金监督规范的性质尚不明晰,但是理论上一般认为监督义务的上位概念即注意义务具有任意属性,允许基金合同予以限缩或免除,但在基金领域,为防加剧基金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及信义规范功能削弱的负外部性,不应允许当事人完全免除。
(1 )私募基金监督规范的性质尚不明晰
《基金法》第36 条、第37 条关于托管人“应当”监督的规定未限定于公募基金,依体系解释似应将私募基金监督规范的性质也界定为强制性规范,但结合基金立法史及基金法理,不应简单地得出这一结论。 首先,基于对受益人自主权的尊重,“除非有特别理由,否则不应对人们的交易强加强制性规则,而是任由其自由支配彼此的关系。” [36]且私募基金作为合格投资者与专业机构之间的特别安排,不涉及公众利益,外部监管的程度亦低于公募基金,因此在未触及信义义务的核心时,应当将其界定为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配制更为妥帖的基金架构及权利义务。 其次,上述托管职责的规定在 2004 年《基金法》只调整公募基金时就已存在,而后在两次修法过程中一字不落地沿用至今,若基于体系解释将公募基金托管职责的规定完全适用于私募基金可能不尽合理,例如私募股权基金缺乏公共存管部门公示信息,一旦基金资产从托管账户转至融资账户,托管人实质上即丧失了监督能力,再如非标投资中,托管人也无需复核基金净值。此种情形下若要求托管人对其无法监督的事项履行监督义务,明显超出了托管制度的立法意旨。 再次,《基金法》第 88 条规定“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确立了私募基金约定优先的规则,虽未明确此规则是否适用于监督义务,但仍存有解释空间。 最后,对于这一问题两大协会之间也存在极大争议。根据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第 4 条第1 款,托管人的法定监督职责不得被基金合同与托管合同免除[37]。与此相反,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指引》第7 条及第15 条明确,私募基金合同可自由变更托管人的法定监督职责,甚至更进一步地将私募基金的监督规范界定为选择适用规范,即未经合同选入,托管人不承担相应监督职责。[38]综上所述,私募基金领域的监督规范性质尚不明晰,需要结合学界的通说观点,从监督义务的上位概念注意义务出发,通过界定其规范性质,进而确定监督义务能否被合同免除以及免除的边界。
(2 )信义规范不得适用自由免除规则
对于信义义务是建立在财产法基础还是合同法基础上以及其能否被合同限缩,是过去一百年里学者争议的重要议题[39],并形成了自由免除论和限制免除论两大阵营。自由免除论者认为,信义义务不具有特殊性,而是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基础[40],因此,从法理上讲,信义义务作为合同的特殊条款,自然可以适用合同的免除规则,由当事人任意免除[41]。限制免除论者主张信义关系不仅可以在合同关系下产生,还可能发生在侵权行为、事实行为等基础关系中[42],受信人的地位并非如合同当事人一般平等,行事标准比合同关系要求要高,其所具有的强烈道德色彩以及其内容中所包含的强制性因素也已经超出了合同法的范畴,故信义义务作为法定义务可为当事人减轻但不得彻底排除[43]。
自由免除论之所以呼吁放松或弱化信义义务,其着眼点在于信托的合约性特征,其与限制免除论就信义义务的性质产生争议的核心原因在于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往往存在着交叉与重合,即合同关系与信义关系并非互斥的,而是可能作为两种规范关系存在于同一事实、当事人之间,因此,信义关系往往建立在契约基础上[44]。尤其在商业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亦受到法定义务的约束,如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使得合同义务与信义义务的联系更加紧密[45]。然而,契约关系是平等主体以合意的方式而达到等价交换的制度安排,而信义义务往往发生在不平等的双方之间,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脆弱关系及自由裁量权,需由受信人为受益人利益行事。两项制度从历史渊源、产生方式、救济方式、对价、道德性质等方面均不得等同视之。故信托虽然往往建立在合同基础上,但其本身却并不是合同。在两者重合的情形下,不应形式化地依据合意来确定义务属性,因为合同与信托均存在承诺要素,而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脆弱性、信赖等事实因素以确定义务的性质[46]。
因此,信义义务不应简单适用合同规范的自由免除规则,而应依据信义义务自身的规范性质及内在逻辑确立免除规则。
(3 )监督义务的规范性质及免除规则
虽然信义义务不应简单类比合同规范允许当事人几无限制的排除适用,但就信义规范中的注意义务规范而言,其相较于忠实义务而言尚未“触及信义义务的核心”,故而更多地体现为任意属性。[47]当然,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由弱到强呈现谱系变化[48]。
在公募投资基金中,由于基金相比于信托结构受到更强的外部监管,且基金受托人往往系专业受托人,故即使是采自由免除论的英国法,也明确规定排除基金托管人注意义务的条款无效[49]。然私募基金强调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对基金架构“量体裁衣”,部分免除监督义务(如免除基金托管人对管理人投资行为或者申购赎回的监督),只需充分披露即可。[50]当然,注意义务的免除并非绝对不受限制,至少需保留受信人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51],否则可能会产生两项不利后果:一则基金托管人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为监督义务,完全免除监督义务将会使得托管人的义务属性降格为合同义务,如果放任当事人意思自治,排除信义义务的适用,势必破坏信义关系的结构特征,削弱信义义务的价值属性,使得信义法本来作为一项独立于合同法的法律渊源,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更加不易于适用,造成信义规范削弱的负外部性;二则在金融资产管理领域,私募基金的外部监管较弱,投资人在认购/ 申购基金份额时,往往是对于格式化的私募基金文本表示同意,其本身对于基金文本中免责条款所指向的后果无法全面知悉,自然也无能力作出真实的同意表示,一旦允许基金合同完全免除监督义务,托管人定会尽一切可能促使投资人同意该等免责条款,投资人更加难以获取全面、真实、准确的资料,即使履行形式上的知情同意程序亦难以有效维护其利益,如此一来,基金治理失衡更加难以避免。
(4 )私募股权基金应受基金法规范
就私募股权基金[52]托管人是否受基金法规范而负有信义义务,还是其责任仅以合同为限,两大协会争议极大,理论及实务界亦存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从《基金法》第72 条及法律名称的文义解释角度认为私募股权基金不受《基金法》规范[53],托管人责任以合同约定为限,实践中亦有相当数量的案例采类似观点,如(2019) 鲁01 民终8544 号、(2018) 京0102 民初40684 号、(2019 )豫0191 民初24797 号案等。另一种观点则或是基于私募股权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无本质差别,或是基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与《基金法》之间的关系,认为私募股权基金亦应适用《基金法》[54],实践中采类似观点的案例参见(2019 )津01 民终3107 号、(2017 )川01 民终12773 号案等。
本文认为,私募股权基金应适用基金法,理由如下: 第一,两种基金虽然在募集对象、募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契约型基金中,两者的法律关系一致,均采双受信人制,基金托管人的法律地位都是信托受托人,不得仅仅因为前述程序性差异而适用不同的规范内容,且当下私募股权基金托管人的监督义务因无法可依而降格为合同义务,投资者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实践中私募基金合同往往以《基金法》作为蓝本,亦客观上反映了私募基金领域对《基金法》的认同与需要。故从制度供给的角度考虑,也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诠释方法。 第二, 2012 年《基金法》修订时本欲纳入私募股权基金,但基于我国的分业监管模式,当时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权归属于多个政府部门,修法的阻力较大[55],僵持之下,最终基金法未明确规定私募股权基金。然在2013 年之后,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权已统一归到证监会[56],此种分业监管的障碍已不复存在。 第三,通过扩大解释《证券法》第 2 条中的“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将私募股权基金纳入《基金法》的适用范畴也存有可行性; 第四,证监会制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 1 条、第2 条明确其系依据《基金法》制定,然其适用范围却不仅包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还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第五,统一规范两种基金在比较法上亦是立法趋势。 2008 年以前,私募投资基金与公募投资基金主要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然而在金融危机及麦道夫事件发生后之后,两者的法定规定逐渐趋同[57]。例如,欧盟UCITS 主要规范公募基金,AIFMD 指令主要规范私募基金,但两者在基金托管人的资质要求、合同内容、监督职能等内容上基本一致。
3. 信义规范的补充适用
由于基金法仅有限列举了托管人的监督职责,若某一监督事项基金合同与托管合同未做约定或约定不明,此时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能否补充适用信义规范。对此,虽有观点主张托管人的监督义务以合同约定为限[58],银行业协会公布的《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指引》第15 条第1 款亦将托管人的监督职责限于法律明确规定及合同约定,实质上排除了信义规范的补充适用空间。但是更为符合信托法理的观点认为基金托管人的监督义务不限于合同文本,托管人需依据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履行监督义务。[59]两种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监督规范的性质系缺省性规范还是授权性规范。
根据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 柴芬斯及美国学者梅尔文. 艾伦. 艾森伯格的观点,法律规范可划分为强制性规范(mandatory rules )、缺省性规范(default rules )及授权性规范(enabling rules ),其中授权性规范仅在当事人明确选入后才得适用,缺省性规范则除非另有约定否则自动适用,后两种均系任意性规范。一般认为,信义规范在适用时,基于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当事人未明确排除,则应当自动适用[60],故将其界定为缺省性规范而补充适用于合同及法律未规定之处更为符合信托法理。
然而,并非所有未明确规定的监督事项均应补充适应信义规范,若某一事项(例如止损及强制平仓[61])明显超出托管人的监督能力或者监督成本显著过高,则即使从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亦不应将该等事项列入托管人的监督范围,以免过分加重托管人的责任,促使托管人的逆向选择,如此反不利于投资人的利益保护,也与有限的托管费率并不相符。
经总结司法判例、比较法及监督事项的各项要素(具体包括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监督能力、监督成本、托管费率、法律风险、外部监管强度、涉众性等七项要素),本文认为,托管人的职责范围至少还包括对募集行为、管理人持续运营状态的监督。
(1 )募集行为的监督
现行法未明确将募集行为纳入托管人监督范围,实践中亦操作不一。在(2018 )粤03 民终16127 号、(2019 )京02 民终8082 号、(2019 )湘02 民终2409 号案中,法院认为托管人在执行划款指令时须对基金的成立条件及备案情况进行审查,以确定其具有托管权限。但(2016 )浙06 民终4190 号案则以基金合同约定为限,将基金募集行为排除在监督职责范围之外。
对此,本文认为,根据《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第2 条第1 款,基金托管人不属于募集机构,其本身也不参与基金募集,且基金财产在由募集账户转入托管账户前,托管人与投资人尚未建立信托关系,由此观之,似乎托管人不应审查管理人的募集行为。不过,募集行为决定了托管人是否取得了托管权限,加之基金财产所有权移转前,其虽未与投资人建立信托关系,但是基于两者之间的信赖关系,托管人仍作为受信人履行监督义务。因此,在签订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托管合同前,托管人应当对合同条款尤其是基金成立条件、基金投资限制等条款进行事前评估[62]。待信托关系建立后,应事后在执行投资指令或者进行投后监督时,对一些明显违法、违约的募集行为承担监督责任,如在执行投资指令时可一并审查基金是否经过备案、是否达到约定募集规模、是否有效成立、基金管理人是否合法注册,以确认托管人是否取得了托管权限。对于管理人是否挪用募集账户的资产、是否进行违规承诺、投资者资质是否适当等其他违法募集行为,除非基金合同与托管合同另有约定(如将基金托管人确定为募集账户的监督机构),否则,鉴于上述事项在托管人监督能力范围之外,加之有募集机构承担相应职责,托管人并无义务进行监督。[63]
(2 )管理人异常运营的监督
基金运作过程中,不仅基金本身可能产生违规问题,基金管理人也可能会出现破产、管理人实际控制人失联等经营异常的情形,对于该等情形,基金业协会要求托管人接管受托职责,承担召集份额持有人会议和保全财产职责的责任,银行业协会则在《商业银行托管业务指引》明确规定托管人不应承担上述监督职责,甚至有权公告解除合同[64]。
本文认为,虽无法律明确规定,托管人亦应对管理人的异常运营状态进行监督,而无权公告解除合同。 首先,管理人的异常运营状态未超出托管人的监督能力范围,基于其受托人地位自然应当承担监督义务 [65],其次,管理人失联并非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托管人也无权公告解除合同,即使基金合同将此作为约定解除条件,亦可能因为违反信义规范中“不可免除的核心”而无效。退一步讲,即使合同解除,基于托管人的受信赖关系及被让渡的权利,其也应当作为受信人履行监督职责。
当然,托管人虽应承担监督职责,但其监督方式绝不包括基金业协会所主张的“接管受托职责”。 接管受托职责的理论基础在于,共同受托人之一死亡时,剩下的受托人基于共同处理事务、共同承担责任的要求应当独自承担全部的受托职责。然在契约型基金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职责迥异、责任独立,基金托管人不应当、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去履行管理人应当承担的职责。此与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不符,更是将管理人的过错转嫁到托管银行内部,不利于托管行业发展。对此,较为符合信托法理的处置方式是由基金托管人 临时止付、冻结基金账户[66]以及时止损,而后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并参考《基金法》第 29 条第1 款“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在六个月内选任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管理人产生前,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临时基金管理人”,由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以决议的方式更换管理人、启动清算程序,在新的管理人选任出之前,由监管机构担任临时管理人。
注释:
[1]《信托法》第32条第2款:“共同受托人之一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他受托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2018年7月23日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告,要求基金托管人在“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托管银行要按照《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切实履行共同受托职责”。参见《关于上海意隆等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风险事件的公告》,载基金业协会,https://www.amac.org.cn/aboutassociation/gyxh_xhdt/xhdt_xhgg/201807/t20180713_241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6月15日。
[3]] 银行业协会主张《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未规定银行共同受托责任,托管银行并不负有“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等法定职责,托管银行依法依规不承担“统一登记私募基金投资人情况”义务,商业银行作为托管机构依法不承担“保全基金财产”的连带责任。参见卜祥瑞:《银行托管私募基金权责清晰,依法依约不承担共同受托责任》,载《金融时报》2018 年7 月26 日第2 版,第1-2 页;巴曙松:《合理界定托管机构的职责范围,促进资产管理业务链的良好合作》,载中国银行业协会,https://www.china-cba.net/Index/show/catid/14/id/19300.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6 月15 日。
除此之外,银行业协会还以颁布行业规范的形式否定了基金业协会对托管人的声讨,其中着重强调规定托管人的托管职责以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为限,而不当然承担连带责任。参见《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指引》(2019 年3 月18 日)第15 条:“托管银行承担的托管职责仅限于法律法规规定和托管合同约定,对实际管控的托管资金账户及证券账户内资产承担保管职责。托管银行的托管职责不包含以下内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托管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一)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二)审核项目及交易信息真实性;(三)审查托管产品以及托管产品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四)对托管产品本金及收益提供保证或承诺;(五)对已划出托管账户以及处于托管银行实际控制之外的资产的保管责任;(六)对未兑付托管产品后续资金的追偿;(七)主会计方未接受托管银行的复核意见进行信息披露产生的相应责任;(八)因不可抗力,以及由于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等)发送或提供的数据错误及合理信赖上述信息操作给托管资产造成的损失;(九)提供保证或其他形式的担保;(十)自身应尽职责之外的连带责任。”
[4]参见赵荣华与上海缠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上海金融法院(2019 )沪74 民终663 号民事判决书;包国君、深圳慧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粤03 民终17646 号民事判决书;黄静与深圳晋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 )豫0191 民初24797 号民事判决书;谭传俊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等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 )京0102 民初40684 号民事判决书;王宁宁等与山东赑贝贸易有限公司等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鲁01 民终8544 号民事判决书;姚振玉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 )京0105 民初73019 号民事判决书。
[5]根据IOSCO的考察,各国基金的组织形态主要包括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SeeIOSCO,Examination of Governance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s,Final Report,PartⅠ,§5 (2006).除此之外,在一些法域如美国、我国还包括有限合伙型基金。
[6]契约型基金依照基金契约数量的不同,可分为“一元模式”、“二元模式”以及印度别具特色“受托人委员会”等模式,其中,“一元模式”根据当事人地位及托管人职责的不同,还可分为日本法上的一元信托和英国法上的双受信人制。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全国人大官方网站释义;又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释义》(第2 版),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9 页。
[8]参见陈向聪:《信托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4 页;闫海,刘顺利:《独立与制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法律地位的重构》,载《浙江金融》2012 年第6 期,第76 页;李江鸿等:《商业银行托管业务法律问题与法律风险》,载《金融论坛》2012 年第5 期,第40 页;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301 页;汤欣,范晓语:《私募基金托管人职责与相关争议的法律适用》,载《投资者》2018 年第4 期,第219 页;梁清华:《论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的重构》,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9 期,第54 页;姜涛,尹亮:《证券投资基金信托:模式选择与立法建构》,载《财经科学》2005 年第3 期,第36 页;汪灏:《证券投资基金组织形态研究》,武汉大学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5 页。
[9]《中基协洪磊:推动双受托人制度在私募基金业落地》,载央广网http://was.cnr.cn/was5/web/detail?record=1&primarykeyvalue=DOCID1%3D%27524295090%27&channelid=282695&searchword=%E4%B8%AD%E5%9F%BA%E5%8D%8F%E6%B4%AA%E7%A3%8A&keyword=%E4%B8%AD%E5%9F%BA%E5%8D%8F%E6%B4%AA%E7%A3%8A ,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6 月15 日。
[10]参见[日]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张军建,张雁辉:《信托法中共同受托人概念之考察》,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67页。
[11]《基金法》第145条第2款:“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本法规定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2]参见洪艳蓉:《论基金托管人的治理功能与独立责任》,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251 页;王猛,焦芙蓉:《私募基金托管人的法律地位和责任边界——以投资人诉托管人侵权案为例》,载《中国证券期货》2019 年第2 期,第76 页;胡伟:《论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我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 为视角》,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 年第3 期,第80-83 页;刘燊:《论投资基金托管人制度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09 年第7 期,第35 页;王国刚:《公司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组织模式的基本选择》,载《财贸经济》2002 年第10 期,第19 页;沈达明:《衡平法初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2 页;方嘉麟:《信托之理论与实务》,台湾月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0 页;文杰:《证券投资基金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版,第73 页;郭锋,陈夏:《证券投资基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96-97 页。
[13]参见徐琳琪:《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8-29 页。
[14]参见陶伟腾:《基金托管人之义务属性辨析:信义义务抑或合同义务?》,载《南方金融》2019 年第10 期,第96 页;王沛然:《论基金托管人的责任认定: 一种回归合同安排的视角》,载《证券法苑》2020 年第2 期,第460 页。
[15]参见张国清:《投资基金治理结构之法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52 页。
[16]参见王涌:《信义义务是私募基金业发展的“牛鼻子”》,载《清华金融评论》2019 年第3 期,第58 页;王苏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22 页。
[17]参见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97 页。
[18]See Gartside v. Isherwood , 1 BrO.C.C. 668, 560 (1788).
[19]See Hospital Products Ltd v. 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oration, HCA 64, 156 CLR 41, 96-7 (1984); s ee also Galambos v. Perez, 3 SCR 247, 249 (2009).
[20]SeePaul B. Miller, A Theory of Fiduciary Liability , McGill Law Journal, Vol.56 2011.
[21]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9;又见[美]安德鲁·S.戈尔德、保罗·B.米勒编著,林少伟、赵吟译《信义法的法理基础》,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0-84页。
[22]See Alastair Hudson, Un derstanding Equity & Trusts (3rd edition ), Routledge-Cavendish , 2008, p.67; 又见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88 页。
[23]参见彭插三:《信托受托人法律地位比较研究——商业信托的发展及其在大陆法系的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3 页。
[24]参见王苏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 页。
[25]参见薛波主编、潘汉典总审订:《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549-550 页;王苏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 页。
[26]参见沈达明:《衡平法初论》,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7 年版,第174 页;[ 美] 安德鲁·S. 戈尔德,保罗·B. 米勒:《信义法的法理基础》,林少伟,赵吟译,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76 页。
[27]参见王涌:《信义义务是私募基金业发展的“牛鼻子”》,载《清华金融评论》2019 年第3 期,第56 页。
[28]See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v. Smith , FCA 375 (1991 ); 又见[ 美] 安德鲁·S. 戈尔德,保罗·B. 米勒:《信义法的法理基础》,林少伟,赵吟译,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93 、246 页。
[29]参见文杰:《证券投资基金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版,第73 页;郭锋,陈夏:《证券投资基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96-97 页;刘燊:《论投资基金托管人制度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09 年第7 期,第36 页;沈达明:《衡平法初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2 页;方嘉麟:《信托之理论与实务》,台湾月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0 页;洪艳蓉:《论基金托管人的治理功能与独立责任》,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251 页。
[30]参见何宝玉:《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169 页;吴晓灵:《投资基金法的理论与实践——兼论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与完善》(第2 版),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19 页。
[31]See Trustee Act 1956 , §50 (1956 ); Mauritius 2001 The Trusts Act , §25 (2001 ).
[32]See Arning v. James , Ch. 158 (1936 ).
[33]See Kam Fan Sin,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Unit Trust, Clarendon Press, 1997, p.50; Geraint Thomas and Alastair Hudson, The Law Of Trus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404-1408.

[34]“阜兴系案”基金合同对托管人监督职责作出如下变动:“托管人对委托资产进入其他资管计划(或委托银行贷款账户、或合伙企业等)后的流向及其后的任何资金运作及投资均不承担监管职责”。
[35]参见[ 美] 安德鲁·S. 戈尔德,保罗·B. 米勒:《信义法的法理基础》,林少伟,赵吟译,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39 页,“至于考虑他人利益的内涵,则可以通过对受信人默认的忠义义务和注意义务以及一系列实施性附属规则等予以确定。 双方可以通过协议对这些义务加以细化,只要不免除受信人须善意和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动的义务即可。”
[36]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95.
[37]《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2019版)》第4条第1款:“私募投资基金托管人应当严格履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章规定的法定职责,不得通过合同约定免除其法定职责。”
[38]《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指引》第7 条:“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的服务内容,可以通过合同选择性地约定以下内容:
(一)资产保管服务。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托管合同约定,安全保管托管银行可控制账户内的托管资产;未经相关当事人同意,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分配托管资产。
(二)账户服务。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托管合同约定,为托管资产开立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基金账户、期货账户等,并负责办理相关账户的变更、撤销等。
(三)会计核算(估值)服务。根据托管合同约定的会计核算办法和资产估值方式,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托管资产单独建账,进行会计处理(估值)、账务核对、报告编制等。
(四)资金清算服务。根据托管合同约定,执行托管账户的资金划拨、办理托管资产的资金清算等事宜。
(五)交易结算服务。根据投资标的市场交易结算规则和托管合同约定,办理托管资产的结算交收等事宜。
(六)投资监督服务。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托管合同约定,对托管资产的投资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包括托管账户的资金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收益计算及分配等情况。
(七)信息披露服务。根据法律法规、行业协会规定以及托管合同约定,将托管合同履行情况和托管资产的情况向相关当事人履行披露和报告义务。
(八)公司行动服务。根据托管合同约定,向相关当事人提供托管资产持有证券的公司行动信息,以及根据委托人指令(如有)代为行使证券持有者权利。
(九)依法可以在托管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
《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指引》第15 条:“托管银行承担的托管职责仅限于法律法规规定和托管合同约定,对实际管控的托管资金账户及证券账户内资产承担保管职责。托管银行的托管职责不包含以下内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托管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一)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
(二)审核项目及交易信息真实性;
(三)审查托管产品以及托管产品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
(四)对托管产品本金及收益提供保证或承诺;
(五)对已划出托管账户以及处于托管银行实际控制之外的资产的保管责任;
(六)对未兑付托管产品后续资金的追偿;

(七)主会计方未接受托管银行的复核意见进行信息披露产生的相应责任;
(八)因不可抗力,以及由于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等)发送或提供的数据错误及合理信赖上述信息操作给托管资产造成的损失;
(九)提供保证或其他形式的担保;
(十)自身应尽职责之外的连带责任。”
[39]See Melanie B. Leslie, Trusting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and the Limits of Default Rules, Working Paper No. 111 Benjamin N. Cardozo School of Law Jacob Burn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2005, p.5.
[40]参见[ 美] 安德鲁·S. 戈尔德,保罗·B. 米勒:《信义法的法理基础》,林少伟,赵吟译,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0 页;S ee Hospital Products Ltd v. 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oration , HCA 64, 156 CLR 41, 96-7 (1984 ).
[41]See John H. Langbein, The Contractarian Basis of the Law of Trusts , l05 YALE L.J. 34, 1995, p.629.; See also Armitage v Nurse , Ch 241 (1998 );See also Trustee Act 2000 , Schedule 1, 7.
[42]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20.
[43]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20;See also Plowright v. Lambert, 52 LT 646 at 652 (1885); See also Alastair Hudson, Understanding Equity & Trusts(3rd edition), Routledge-Cavendish, 2008, p.180;See also Uniform Trust Code, §1008 (2010);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of Trusts, §96 (1)(a).
[44]参见彭插三:《信托受托人法律地位比较研究——商业信托的发展及其在大陆法系的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8 页。
[45]参见彭插三:《信义法律关系的分析及适用》,载《湖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3 期,第202 页。
[46]参见彭插三:《信托受托人法律地位比较研究——商业信托的发展及其在大陆法系的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9 页。
[47]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95; see also Melanie B. Leslie, Trusting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and the Limits of Default Rules, Working Paper No. 111 Benjamin N. Cardozo School of Law Jacob Burn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2005, p.6.
[48]参见陶伟腾:《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6页。
[49]Se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 §253 (2000 ), “获授权单位信托计划信托契约的任何规定,如免除管理人或受托人在行使计划相关职能时因未尽应有的谨慎和勤勉义务而承担的责任,则该规定无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共同基金)条例》第15 条亦规定基金合同不得免除、甚至不得限制基金托管人的义务;See Securitie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Mutual Funds )Regulations (amended 2021 ), §15, “任何信托契约都不得包含具有以下效力的条款: (i )限制或取消与任何共同基金或单位持有人相关的信托义务和责任;或(ii )赔偿受托人或资产管理公司因其疏忽行为或作为或不作为给单位持有人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50]Tamar Frankel 教授亦认为在信义规范的选出时应当遵循知情同意程序,且此种同意的意思表示须明确且具体,具体而言,信义规范通过以下方式选出:第一,受托人必须告知委托人,在特定条件下其已不再是受信人;第二,委托人应有独立自主的判断能力;第三,委托人取得了完整信息;第四,委托人对交易的同意表示明确且特定;第五,交易实质条件对委托人公平合理。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p.200-p.207.
[51]See Alan Newman, Trust Law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hallenges to Fiduciary Accountability, 29 Quinnipiac Probate Law Journal 2016,p.264.
[52]基金业协会认为《基金法》可得约束私募股权基金,参见《关于上海意隆等4 家私募基金管理人风险事件的公告》,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https://www.amac.org.cn/aboutassociation/gyxh_xhdt/xhdt_xhgg/201807/t20180713_2410.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6 月15 日。银行业协会认为私募股权基金不受《基金法》调整,而应以合同为限确定其责任。参见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法律顾问卜祥瑞:《银行托管私募基金权责清晰,依法依约不承担共同受托责任》,载《金融时报》2018 年7 月26 日第2 版,第1 页。
[53]参见倪受彬:《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托管行的地位与责任》,载《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 年第5 卷,第480 页;吕海宁:《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4 页;徐琳琪:《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8-29 页。
[54]参见洪艳蓉:《论基金托管人的治理功能与独立责任》,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254 页;赵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1 页。阮昊:《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一体规范》,载《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1 期,第108-109 页。
[55]2012 年,《基金法》的修订草案进入审议阶段后,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协会等25 家行业协会集体上书,认为私募股权基金纳入《基金法》不利于行业发展,有鉴于此,最终通过的《基金法》未规定私募股权基金。
[56]《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13 年6 月):“证监会负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督管理,实行适度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拟订促进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政府对私募股权基金出资的标准和规范。”
[57]参见阮昊:《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一体规范》,载《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1 期,第110-112 页。
[58]参见王沛然:《论基金托管人的责任认定: 一种回归合同安排的视角》,载《证券法苑》2020 年第2 期,第460 页。原文将信义规范的性质表述为缺省性规范,然其实混淆了缺省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缺省性规范系指推定适用规范,未经合同选出自动使用,授权性规范系指选择适用规范,未经合同选入不得适用。
[59]参见倪受彬:《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托管行的地位与责任》,载《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 年第5 卷,第480 页;张国清:《投资基金治理结构之法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3 页。
[60]参见[ 美] 安德鲁·S. 戈尔德,保罗·B. 米勒:《信义法的法理基础》,林少伟,赵吟译,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34 页。
[61]基金法未对的监督义务进行规定,而在实践中常会发生此类争议,在(2020)京02民终463号案中,基金合同特别约定,在净值跌破止损线时,管理人负有平仓义务,但是托管人对管理人的此项行为不负有监督义务,法院最终以合同为依据判定基金托管人不负有止损义务。此案是基金合同明确约定了排除条款,然在基金合同与托管合同未明确否定托管人的止损监督义务时,此时基金托管人是否负有此项监督义务?对此,本文认为,止损及强制平仓义务系典型的管理职责,需要管理人核对基金所投证券的每日净值以确定是否低于预警线和止损线,此项事务已然超出了基金托管人的业务范围且监督成本显著过高,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否则基金托管人原则上不应承担对证券止损的监督义务。
[62]《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15 条:“基金托管人在与基金管理人订立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托管合同等法律文件前,应当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角度,对涉及投资范围与投资限制、基金费用、收益分配、会计估值、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条款进行评估,确保相关约定合规清晰、风险揭示充分、会计估值科学公允。在基金托管合同中,还应当对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业务监督与协作等职责进行详细约定。”
[63]域外法中亦有法规确认托管人对募集行为的审查义务,如欧盟UCITS 指令及其实施细则即规定,“存管人应确保基金单位或份额的销售、发行、回购、赎回和撤销系根据相应法律法规以及基金的组织性文件执行,确保并定期检查基金单位或份额的销售、发行、回购、赎回和撤销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组织性文件要求,且此类程序得到了有效实施。”See 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Directive ,§22.3. (a )(2014 ); UCITS Regulation , §4 (2016 ).
[64]《商业银行托管业务指引》第13 条:“托管银行发现委托人、管理人有下列情形的,有权终止托管服务:……(三)被依法取消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质或经营异常;(四)被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依法宣告破产或失联……”
[65]实践中亦有案例采类似观点,该案以托管人未调查到管理人破产事实为由,基于公平原则课以其15%的补充责任,参见南京中院(2020)苏01民终4506号案。但本文认为上述案件的裁判思路有误,给基金托管人课以法律责任,实际上无需借道公平原则,而可基于托管人的信托受托人地位补充适用信义规范。
[66]基金托管人仅得对托管账户内的基金财产实施保全措施,对募集阶段的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及投资后的融资账户,既无权利也无能力进行保全。参见张国蓉,张辛茹:《浅议私募投资基金托管人的责任边界》,载《中国城市金融》2018 年第9 期,第66-67 页。
“金融汇”栏目由李皓律师主笔/主持,每周一与“证券法评”栏目交替发布。我们希望借此搭建金融法律实务交流的平台。如您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点击文末留言。
向“金融汇”栏目投稿,欢迎发送邮件至:
lihao@tiantonglaw.com
《民法典》第65条商事登记公示效力研究 | 金融汇
《民法典》框架下“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解释
再论结构化信托业务中的法律关系
金融消费者保护案例研究报告
信托纠纷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
刑民交叉课题续篇: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影响——以穿透式审判为语境
信托业务中股权让与担保性质认定及权利义务分配
信托关系下财产的保全与执行问题
信托纠纷中的“刚性兑付”及其效力体系
信托业务中第三方增信措施的性质及效力认定
上市公司纠纷研究:股东临时提案的审查争议
《九民纪要》对票据审判的影响
金融业务中的赋强公证制度
上市公司纠纷研究:担保无效、越权代表及过错认定
上市公司纠纷研究:关联交易、忠实义务及董事责任
委托贷款形式下职业放贷行为的效力认
是时候重新理解《民诉法》227条了
2019年度上市公司诉讼观察(下)
2019年度上市公司诉讼观察(中)
2019年度上市公司诉讼观察(上)
抵押与租赁冲突时的顺位认定与救济
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与抵押权的冲突与反思
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下)
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中)
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上)
详解执行异议之诉中的保证金质押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的冲突与协调——以保全程序对在先确权案件的冲击为视角
债券违约关键角色 ——“债券持有人会议”与“受托管理人”核心法律问题
原状分配:一种典型的信托财产清算方式
《九民纪要意见稿》——当营业信托遇上金融消费者
赋强公证制度在信托业务领域中的几点问题
再论结构化信托中的法律关系问题:以(2017)最高法民终604号案为切入点
信托公司常见执行纠纷问题 ——以案外人排除执行的若干权利为视角
常见信托业务中的非典型增信措施——以第三方回购及差额补足协议为例
通道类信托业务——实体法律关系与受托人责任分析
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不完全操作指南
课题结项篇: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路径选择
刑民交叉案件中金融机构常见过错类型及其法律风险
刑民交叉案件中不同刑事罪名对民事诉讼的影响差异——以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
涉犯罪合同效力问题的实务认定
刑民交叉中刑事追缴、退赔与民事诉讼的冲突与协调
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以笔录供述为重点
刑民交叉案件中,到底何时应中止审理?(含相关规定及典型案例)
金融机构刑民交叉案例专项研究系列之一——案例大数据研究报告
论新型商事交易结构中的合同解析及解释路径
虚假应收账款质押若干问题探析
试析银行内部人员职务行为认定的司法标准
通道方不起诉,出资人能直接提起诉讼吗?
被保全人索赔时,保险公司应如何参与和控制抗辩程序?
融资租赁案件中名实不符的表现形态及其法律分析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民事责任探析
一文看懂利息、罚息与复利
债券违约中的承销商虚假陈述责任及其诉讼风险应对
保证人应否为保理商的疏忽“背锅”?——“假保理”中的保证人减责路径分析
“假保理”中保理商向债务人追责的路径选择
解构有追索理中同时起诉的难题
试评“骗贷”中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 ——《合同法》52条第3项的过去与《民法总则》149条的未来
标签: 美国证券法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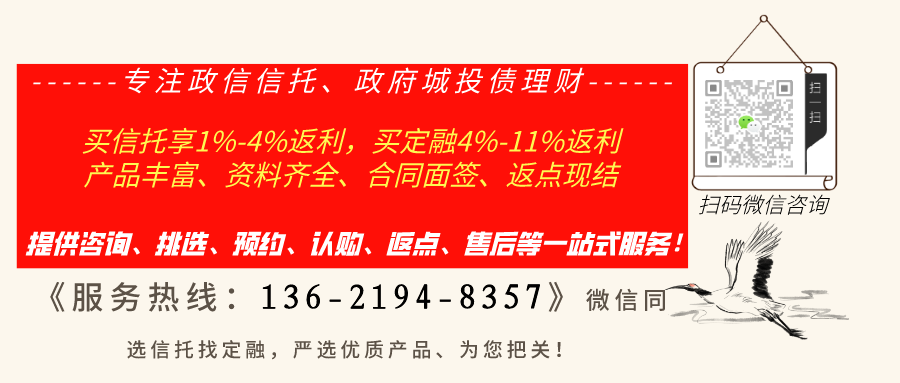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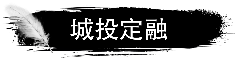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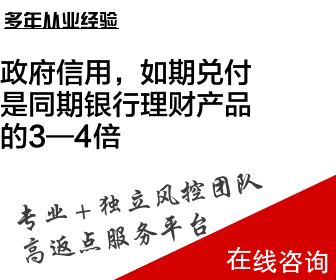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